

8月30日的徐汇西岸,江风携夏末余热,波光与灯火糅成流动的画。随着郎朗的指尖落琴,《爱乐之城》的旋律顺着江面漫开,瞬时点燃气氛——此时,音乐成了所有人共通的语言。
这不仅是一场即兴的街头演奏,这一天,更是“郎朗音乐世界”正式落户徐汇西岸的日子。从指尖跃动的旋律到落地生根的音乐教育空间,郎朗将对古典音乐的热爱与坚守,深深扎根在了这片兼具艺术气息与科技活力的土地上,也勾勒出古典音乐融入当代生活的新图景。

音乐不是孤立的
上观新闻:您在西岸的开放空间演奏《爱乐之城》时,现场观众的投入度远超预期。选择把“郎朗音乐世界”落在这里,应该不只是因为西岸的人气,更有对音乐教育场景的深层考量吧?
郎朗:真正吸引我的是西岸“艺术与生活共生”的氛围。现在很多音乐教育机构把自己关在封闭的琴房里,孩子学琴就像完成任务,很难感受到音乐和生活的联系——但西岸不一样,这里有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还有绵延的滨江步道。孩子来学琴时,下课后能沿着黄浦江散步,听江风,看晚霞,这种“沉浸式”的艺术环境,能让他们从心里觉得音乐不是孤立的。
我之前常来西岸,来这里,脑子里会不自觉蹦出几段旋律——音乐创作需要灵感,而自然与艺术交织的环境就是灵感最好的土壤。我们把琴房、演奏厅放进这样的空间里,就是想让孩子们觉得学音乐是一件轻松的事,而不是走进一个严肃的“考场”。能在这样的地方落户,对我们来说是幸运,更是责任。
上观新闻:西岸的“艺术与生活共生”,这种氛围确实和传统音乐厅的严肃感形成反差。“郎朗音乐世界”会不会特意弱化教学感,强化生活感?
郎朗:我们在空间设计上最核心的理念就是“无边界”——打破琴房与公共空间的隔阂,让音乐能自然地“流”出来。比如一楼我们设了一个开放式演奏区,没有舞台,就放一架白色钢琴,不管是学生、老师,还是来参观的市民,只要想弹,都能坐下来弹一曲。
还有二楼的音乐体验区,我们没放传统的乐理挂图,而是做了互动屏幕——孩子能看到音符对应的钢琴键发光,还能听到不同乐器演奏这个音符的声音。我们想让孩子觉得,音乐不是需要坐在课桌前学的知识,而是能摸得到、听得见、玩得起来的乐趣。

上观新闻:西岸本身有很多艺术机构,比如美术馆、剧场,“郎朗音乐世界”会不会和这些机构联动,打造“音乐+”的融合体验?
郎朗:单一的艺术形式容易让人审美疲劳,但不同艺术之间的碰撞,能让孩子更全面地理解“美”。我一直觉得,艺术是相通的。一个孩子如果只学钢琴,可能只会关注是否弹对了音符,但如果他接触了绘画,就会懂得如何用指尖表达色彩感;接触了戏剧,就会懂得如何用演奏传递角色情绪。西岸有这么好的艺术资源,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给孩子打造一个全方位的艺术成长环境,而不只是一个钢琴培训班。
热爱先于技巧
上观新闻:家长送孩子学音乐,出发点各不相同。您觉得艺术教育最该坚守的核心是什么?
郎朗:核心肯定是“热爱”,没有热爱,一切都是白搭。我见过太多孩子,一开始学琴学得好好的,后来因为家长逼得太狠,反而讨厌音乐,甚至看到钢琴就害怕——这太可惜了,本来音乐是给人带来快乐的,结果变成了负担。
我儿子现在4岁多,特别喜欢唱歌,一首儿歌能没完没了地唱,旋律记得比我还准。但你让他坐下来弹钢琴,他根本坐不住,一会儿要去玩玩具,一会儿又要画画。不过,他会主动跟我说“爸爸,我想弹出你那样的声音”,这说明他有兴趣,只是还没到能专注学琴的阶段。我不会逼他,要是现在就把他按在钢琴前练琴,说不定他以后就不喜欢音乐了。
学音乐就像打游戏,为什么孩子愿意打游戏?因为能从中获得快乐,过了一关想过下一关。学音乐也得这样,先让孩子感受到快乐。比如弹一首简单的《小星星》,让他觉得“我能弹出好听的声音”,这种成就感才是坚持下去的动力。
现在很多家长的误区是急功近利,刚学半年就问“什么时候能考级”“什么时候能上台演出”,根本不管孩子喜不喜欢。其实学音乐不是为了考级,也不是为了以后当音乐家,而是为了让孩子多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多一份精神寄托。就像有的人喜欢跑步,不是为了拿冠军,而是为了享受奔跑的快乐——音乐也该是这样。

上观新闻:您说音乐教育要因人而异,毕竟每个孩子的性格、天赋都不同,您心中理想的音乐教育体系是怎样的?
郎朗:完全理想的教育体系很难有。正如你说的,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内向,不爱说话,但弹钢琴的时候特别投入,这种孩子就不能逼他上台表演,得先让他在音乐里找到自信,再慢慢引导他表达;有的孩子外向,喜欢表现,但弹琴的时候容易浮躁,就得让他沉下心来,感受曲子里的细节。
我们的教学方法,首先是“轻量化”,不会让孩子死记硬背乐理,也不会每天逼他们练几个小时。比如教小一点的孩子,会用游戏的方式教他们认音符——把do、re、mi做成卡通卡片,让他们在玩的时候记住;教他们弹简单的曲子,会先讲曲子里的故事,比如弹《卖报歌》,先跟他们说旧社会卖报小孩的生活,让他们带着情感去弹。
另外,我们特别注重“全面性”,不希望孩子只当个弹琴机器。除了练琴,还会让他们听不同风格的音乐,比如古典、爵士、民族音乐;会带他们去听音乐会,让他们感受现场氛围;甚至会让他们尝试作曲,哪怕只是写一段简单的旋律。音乐是活的,要是只盯着技巧,弹出来的曲子也是死的。就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不是只弹对音符就行,得弹出那种“月光洒在海面上”的意境,这需要孩子有感受力、有想象力,而这些不是靠死练能练出来的。
上观新闻:您的学校会针对留守儿童、自闭症儿童开展公益音乐教育,为什么会关注这些特殊群体?在教他们的过程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
郎朗:艺术是公平的,这点在这些孩子身上体现得最明显。不管是留守儿童,还是自闭症儿童,在钢琴面前,他们都是平等的——弹得好就是好,弹得不好也没人会苛责,音乐不会因为他们的家庭背景、身体状况就区别对待。
我记得有个自闭症小孩,一开始根本不跟人交流,也不愿意碰钢琴。我们的老师没逼他,只是每天在他面前弹《小星星》,弹了一个月后,他突然伸手碰了碰琴键,发出了“do”的声音。从那以后,他每天都会主动来练琴,虽然话还是少,但弹钢琴的时候,眼睛里是有光的。还有个留守儿童,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家里条件不好,但他特别有天赋,练琴特别刻苦,现在已经能弹《牧童短笛》了。这些孩子让我觉得,艺术教育不是精英教育,每个孩子都有享受音乐的权利,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能触摸到钢琴,感受到音乐的美好。
我们的公益课有个规矩:每个孩子都必须动手弹,不能只坐着听。因为光听是没用的,只有自己弹出来,才能真正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就像喜欢足球,就得自己上场踢两脚,才能知道奔跑的快乐;喜欢音乐,就得自己弹出旋律,才能知道指尖传递的情感。对这些孩子来说,音乐可能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现状,但能在他们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让他们在难过的时候、孤独的时候,有一份精神寄托。
古典音乐也可以“潮”
上观新闻:这些年您尝试了很多跨界合作,比如和电影、娱乐行业合作,甚至出了跨界专辑。做这些尝试,是不是为了让古典音乐更“接地气”?市场对跨界的接受度如何?
郎朗:对,跨界确实是为了让更多人接触古典音乐。现在的年轻人获取信息的方式太多了,要是还守着“只有音乐厅里的才是古典音乐”的想法,只会把他们推得越来越远。所以我想试试,能不能把古典音乐放进他们熟悉的场景里。比如,《爱乐之城》里的旋律,很多年轻人都听过,我在西岸弹这首曲子,就是想让他们知道这也是古典音乐的一种表达;再比如出跨界专辑,把古典曲子和流行元素结合,让他们觉得“古典音乐也能这么‘潮’”。
不同市场的接受度并不一样。美国和中国的听众比较开放,能接受跨界;德国、法国就比较传统,他们觉得古典音乐就该在音乐厅里听,不能乱改;英国介于两者之间,对跨界的接受度还可以。我新出的《钢琴书2》里,既有纯古典的曲子,也有跨界改编的作品,就是为了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

上观新闻:您在做跨界尝试的时候,会不会担心丢了古典音乐的本色?毕竟有些跨界作品会被质疑“不纯粹”。
郎朗:肯定会担心,但我有自己的底线:不管怎么跨界,都不能丢了古典音乐的根本。比如改编电影插曲,我会尽量往经典风格上靠,让它既有流行的流畅性,又有古典的厚重感;再比如和流行歌手合作,我会要求他们的演唱风格不能太“俗”,要能和古典钢琴的音色匹配。
其实我对艺术是比较保守的,虽然想法多,喜欢尝试新东西,但内心还是觉得经典最珍贵。比如我改编曲子,不会把贝多芬的《命运》改成电子乐,因为那样就丢了曲子里的力量感;也不可能把《梁祝》改成摇滚,因为那样就没了中国音乐的意境。就像制表,要么是纯传统的机械表,要么是纯智能的电子表,没人会喜欢“半机械半智能”的,因为丢了各自的本色。古典音乐也一样,跨界可以,但不能不伦不类,得守住根本,才能让更多人真正喜欢上古典音乐,而不是只图个新鲜。
上观新闻:您之前说“未来会更偏向纯古典音乐”,这是不是意味着您会减少跨界尝试?
郎朗:长远来看,我还是会更偏向纯古典音乐,因为这是我的根。我弹了这么多年古典音乐,它已经融入我的血液里了。而且我觉得,古典音乐的魅力,最终还是要在音乐厅里才能完全展现——比如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只有在音乐厅里,才能感受到那种震撼的力量;听肖邦的《夜曲》,只有在安静的环境里,才能听懂曲子里的温柔。
但我不会完全停止跨界尝试,因为时代在变,古典音乐也得跟着变。比如AI技术,我们可以用它来做配器、做改编,但不能用它来替代演奏;比如流媒体,我们可以用它来传播古典音乐,但不能用它来替代现场演出。尝试新东西不是为了讨好市场,而是为了找到古典音乐和当代生活的结合点,让它能被更多人接受,能传承下去。就像我在西岸演奏《爱乐之城》,不是为了炒作,而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古典音乐可以在街头,可以在江边,可以在任何地方,只要有人愿意听,有人愿意弹,它就能活下去。
本色之美跨越国界
上观新闻:如今AI技术发展迅猛,不少人讨论它对古典音乐的影响,有人认为影响甚微,也有人担忧它会颠覆作曲与演奏模式。从专业视角看,它究竟会给古典音乐带来怎样的改变?
郎朗:AI的能力已经很明显了,它完全能独立作曲,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要说取代演奏者,目前来看可能性不大,未来也很难。大家还是愿意看现场演奏,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共鸣、指尖传递的细微情绪,是AI模拟不出来的——现场感是古典音乐的灵魂之一,这点没法替代。
不过,AI确实能帮上大忙,尤其是在改编、配器这些环节。比如,把一首钢琴曲改成协奏曲,或者给旋律做交响乐化处理、拆分声部,AI能做得又快又精准。之前我试过用AI做配器,效率比人工高很多,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辅助工具。
但也得警惕,别让AI“帮太多”,要是连改编、作曲的工作都被它包揽了,很多从业者可能就没饭吃了,尤其是做幕后创作的人,风险会更大。好在,对演奏者来说,只要还有人愿意走进音乐厅,我们的价值就还在。另外,AI也能帮着提升音乐素养,比如给学生做基础乐理讲解、模拟不同风格的演奏,这些都是积极的一面。

上观新闻:其实,古典音乐的推广始终面临“门槛”问题。在您看来,该如何打破这个门槛,让人们愿意主动靠近古典音乐?
郎朗:推广古典音乐确实有难度,它不是没有门槛,只是很多人把门槛想高了。我以前觉得,好的演奏能让人一听就被打动,根本不需要门槛,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尤其是对从没接触过古典音乐的人来说,里面的西方文化背景、复杂的曲式结构,确实需要一点“入门指南”。就像听中国传统音乐,你得知道《二泉映月》背后阿炳的故事,才能更懂曲子里的悲怆;听贝多芬的《命运》,得稍微了解他苦难的经历,才会明白“命运敲门”的力量。不用懂多深,哪怕只知道一点背景,听的时候感受就会不一样。
其实听中国的古典音乐作品,是打破门槛的好办法。比如《牧童短笛》《梁祝》,旋律里有中国人熟悉的意境,一听就有亲切感。而且中国曲子大多不长,结构也没那么复杂,很适合现在的流媒体传播——大家刷手机的时候,一两分钟就能听完一首,不会觉得枯燥。我之前做了个“中国play list”,把《春节序曲》和《功夫熊猫》里的中国风配乐都放进去,播放量比我预想的高很多。很多年轻人留言说“原来古典音乐也能这么好听”,这说明不是年轻人不喜欢,而是没找到让他们听得懂、有共鸣的方式。
上观新闻:您一直在推动中国古典音乐走向国际,前段时间您还尝试演奏了《笑傲江湖》和《梁祝》。现在国际市场对中国古典音乐的接受度如何?有没有遇到过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
郎朗:现在接受度越来越高了,走势是好的。最明显的是民族乐团,他们去欧洲演出,票房有时候比中国交响乐团还好。为什么?因为民族乐团的音乐是“纯原浆”的——二胡的婉转、琵琶的清脆,都是最地道的中国声音,外国人一听就知道这是中国的音乐,反而容易被吸引。但如果把中国音乐改成交响乐,有时候会显得不伦不类,比如用小提琴模仿二胡的音色,反而丢了原本的韵味,外国人也“get”不到其中的妙处。
用钢琴弹中国曲子也一样,得保留“中国味”。我每年都会出一两首中国曲子的单曲,去年的《雪花》和改编版《摇篮曲》都很简单,没加复杂的和声。因为中国音乐像水彩画,讲究的是意境和留白,要是用油画的技法去“堆色彩”,加太多和声,反而会盖住原本的韵味。比如《牧童短笛》,旋律特别简单,但里面有江南水乡的灵气,外国人也能感受到那种“田园感”。所以关键不是要迎合西方,而是要把中国音乐的本色做好,本色里的美,是能跨越文化差异的。
音乐种子已经种下
上观新闻:您之前说“一天不弹琴就像没吃饭、没洗澡”,对您来说,音乐已经超越了职业的范畴,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能具体说说,音乐对您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吗?
郎朗:音乐对我来说,是精神养分,是情感寄托,也是人生目标。我小时候每天要练琴8个小时,很辛苦,但我从来没觉得累,因为我喜欢。后来成了职业钢琴家,去世界各地演出,见过很多人、听过很多故事,但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有钢琴,我就觉得踏实。
比如我在国外演出,有时候会想家,这时候弹一首《梁祝》,就会觉得特别亲切;有时候遇到不开心的事,弹一首巴赫的曲子,心情就会平静下来。音乐就像我的朋友,不管我开心还是难过,它都能陪着我。而且,通过音乐,我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感受到了很多不同的文化,这些都让我的人生变得更丰富,更有厚度,我要做的是终身的“音乐旅人”。
上观新闻:对于“郎朗音乐世界”的未来,您有怎样的规划?它能够给上海、给中国的古典音乐教育带来什么?
郎朗:我们要做的是把这里打造成“古典音乐人才的摇篮”——和全球最好的音乐学院合作,比如茱莉亚音乐学院、柯蒂斯音乐学院,把它们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引进来,让学员能接受到最专业的教育;还要给学员提供更多舞台机会,比如让他们去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去参加国际钢琴比赛,让他们能走向世界,成为中国古典音乐的“新一代传承人”。
上海是一座有音乐底蕴的城市,古典音乐市场特别好,观众也特别懂音乐。我希望“郎朗音乐世界”能成为上海的一张“音乐名片”,让更多人因为这里而喜欢上古典音乐,让上海成为中国古典音乐的中心。更希望能通过这里,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年轻钢琴家,让中国的古典音乐能传承下去,能走向世界,让更多人听到中国的声音。
我一直相信,古典音乐不是“老古董”,它是活的,是能融入当代生活的。只要我们愿意尝试,愿意坚守,就一定能让它在这个时代里,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就像今天在西岸,江风、灯光、旋律交织在一起,我知道,古典音乐的种子已经在这里种下了,未来一定会开出美丽的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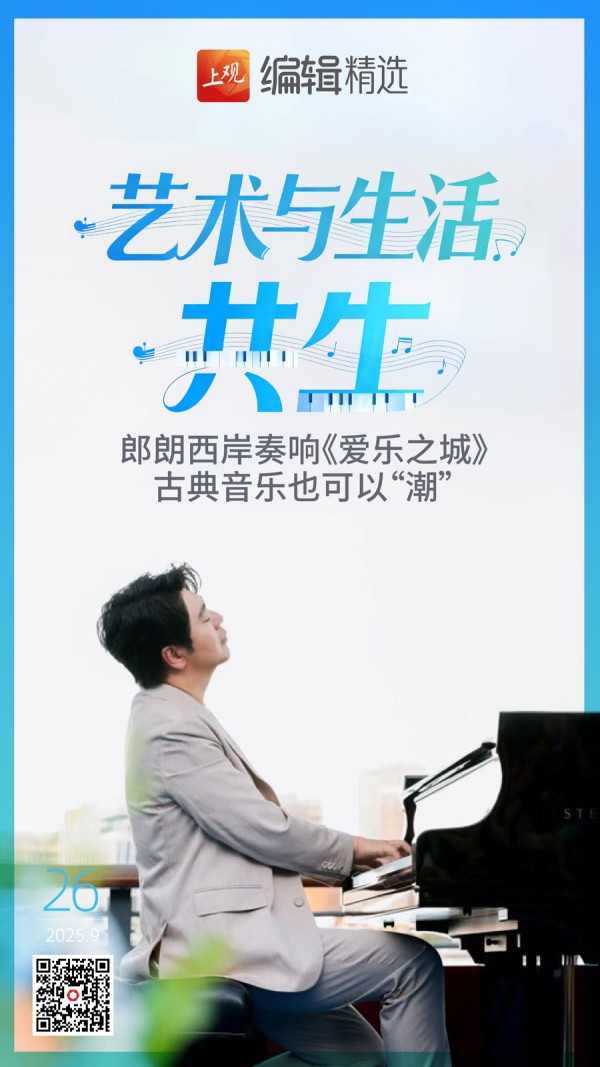 海报设计:曹立媛
海报设计:曹立媛
原标题:《郎朗:我在西岸弹《爱乐之城》,想告诉人们,音乐是活的、能融入当代生活的》
栏目主编:龚丹韵
本文作者:解放日报 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