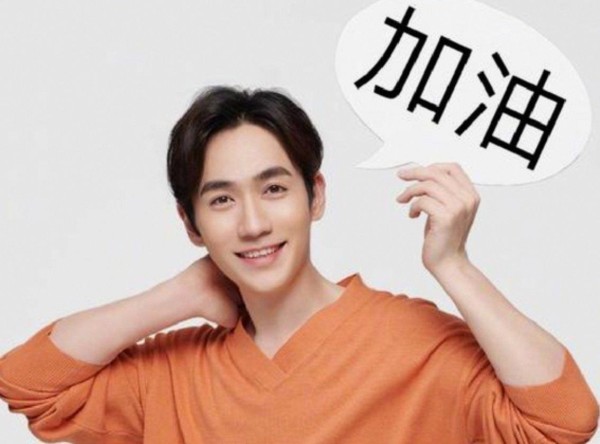网络社会学 |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社会阶层理论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 #生活知识# #社会生活# #社会阶层研究#
文/李雨浛
前言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科林斯(Randall Collins)曾如此评价《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它)之所以受到普及,一是因为它承载了韦伯最出类拔萃的文字,然而其内容又最为平易近人。二是因为它有不同层次的重要性:它既能强烈地感染刚入门的社会学专业学生,也能有力地吸引善于洞察最精致的理论和超理论问题的行家里手。”笔者在阅读时深感自己与兰德尔·科林斯的观点相契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像是一块可以映照解释多种社会现象的金石,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它,必然会得到不一样的收获。人类学者可以从中挖掘出丰富的人类精神史演变材料;社会学者可以领会到韦伯别致而又严谨的研究视角和论证方式;宗教学和哲学学者可以从中汲取行为科学方面的知识;历史学者可以从本书中理解宗教改革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传播学者可以从路德在威登堡大学教堂门口张贴《九十五条论纲》的传播事件追溯而起,研究宗教改革事件的传播路径,讨论为何在传播技术条件如此简陋的十六世纪,新教的教义仍然能像病毒一样扩散传播?
笔者一共花费了三周的时间来阅读这本较薄的“小册子”。在完成本书的阅读之后,笔者又继续阅读了《儒家与道教》、《经济与社会》的部分章节,以补充了解韦伯思想的全貌。

全文字数:5773字
阅读时间:15分钟


一
主要内容与整体框架
全书结构明晰,共分为两个部分、五个章节。在作者引言之后,第一部分“问题”有三章,分别是“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资本主义精神”、“路德的‘天职’观:本书的研究任务”;第二部分名为“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下设“入世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和“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两个章节。
在引言中,韦伯提出了世界文化史的核心问题,即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和与之相伴的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形式是如何起源的。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韦伯在第一章中以大部分商界领袖、资本所有者等商界精英基本上都是新教教徒的实例,探讨了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第一章中,他明确提出,全力以赴的精神、积极进取的精神或者其他可能称之为的精神,这些精神的觉醒都倾向归功于新教教义,而坚决不应该听随一种惯常的趋势,将其与生活享乐相联系,也不要在任何意义上将其与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在第二章中,为了证明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模糊的、无穷无尽的关联,韦伯首先用富兰克林的一席训导之言为据,明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定义,进而探讨基督教历史上诸分支教派各自的特质和相互间的差异。韦伯同时还提出了新的问题:为什么在后资本主义时代,追求物质财富和营利的生活方式被视为一种天职?在14、15世纪的佛罗伦萨,追求财富的态度仍然不被主流伦理认可,至多可以被容忍;然而,在18世纪的宾夕法尼亚,追求财富的态度已经被认为是道德行为的本质。因而,在第三章,韦伯又从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定义回到了针对宗教改革的讨论,通过将路德宗、加尔文宗的教义与天主教教义进行比较,研究路德的天职观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以及加尔文主义在路德天职观基础上的发展。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韦伯对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和浸礼宗诸派四个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形式的天职观进行了描绘,明晰了清教天职观的宗教基础,接着又探究了这一天职观在商业世界中所产生的结果。在文末,身处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韦伯,意识到获取全胜的资本主义有了强大的机器工业作为支撑,不再需要宗教禁欲主义的支持,不免产生了对资本主义世界或将爆发精神危机的忧虑:“没人知道下一个住进这个铁笼的会是谁,或者在这种巨大的发展尽头是否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先知,抑或那些老旧的理想和观念是否会有一个伟大的新生?而如果这两者都不可能,那么是否会在骚动的妄自尊大中渲染出一种机械式的麻木,我们同样不得而知。”在这本意义深远的著作的尾声,韦伯以其对人类现实世界的忧虑作为终章,赋予了本书更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
本书方法论分析
提及韦伯对当代学术界的贡献,除了经典的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理论贡献外,必然绕不开其开创的一套研究方法。韦伯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就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笔者试图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中的内容为例,探讨韦伯使用了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并分析此种研究方法对研究结果造成的影响。
01
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的方法贯穿了韦伯的写作全程。总体来看,韦伯试图通过比较路德宗、加尔文宗以及门诺派、胡格诺派、卫斯理派、循道宗等各个新教派别在宗教伦理上的差异,来解释是宗教如何影响了资本主义发展。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在韦伯自撰的序言部分就有体现:为了说明只有西方的科学真正达到了可以被当代公众认可的发展程度,韦伯就将西方科学在化学、法律、艺术和建筑的等领域中的发展情况与中国、巴比伦和埃及等国进行比较,从而得出了西方科学在公众群体中最具权威的结论。
在具体研究中,韦伯也通过对不同文明宗教信仰的原因、结果以及他们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来确定西方社会和文明的特征。比如,在本书的第三章部分,韦伯就以较长的篇幅论证了路德的天职观与加尔文主义所倡导的天职观二者之间的区别。韦伯写到,“(路德认为)个人应该一直安分地保持上帝安排给他的身份和天职,并且应该根据已经被安排好的身份限制自己的世俗活动……路德不可能在世俗活动和宗教法则之间建构起一种新的,或者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基本的联系……由此可知,路德的天职观仍旧保持着传统主义的性质。他的天职观所指的是人们必须接受的神的旨意,每个人都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一法令。”接下来韦伯又简要介绍了加尔文主义的天职观:“仅仅通过表面的观察就可以发现,对于宗教生活和世俗活动之间的关系,加尔文主义与天主教教义和信义宗教义的看法都完全不同。”最后得出“尽管没有路德个人宗教思想的发展,宗教改革是不可想象的,而且这一改革在精神层面上长期受到路德个人品格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加尔文主义,路德的工作就不可能拥有持久而具体的成功”的结论。
除了在文章的大走向上韦伯坚持他的比较研究方法,韦伯在细微之处同样青睐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佐证他的观点。他举出《神曲》中最后一部分作为例子——诗人寂静地站在天堂里顺从地冥思着上帝的玄妙——将其与被称作“清教主义神曲”的《失乐园》进行对比。《失乐园》的最后一部分,大天使米迦勒对亚当说:“……只要/将你的知识和实践相结合/加上信仰、德行、忍耐、节制,此外还加上爱/就是后来叫做‘仁爱’的,是其他一切的灵魂/这样,你就不会因离开这个乐园而郁郁寡欢/而在你的内心另有一个远为快乐的乐园。”从米迦勒的台词中可以看到,沐浴了宗教改革光辉的清教徒,与十四世纪初的文艺复兴论者相比,更加强有力地表明了自己要重视现世、承认人活在现世中是一种使命的观点。
02
考引实证
理论的提出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韦伯在提出他的观点和理论时也伴随有相应的现世调查数据,“在任何宗教派别复杂的国家中,你只要稍稍留意一下有关职业的数据统计,就能发现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那就是:大部分商界领袖、资本所有者以及那些现代企业中的高级技工和接受过高级技术和商业培训的职员,基本上都是新教徒。”
但是笔者注意到,韦伯在提出支撑其观点的论据时,借用的句式往往是“你只要稍稍留意一下”、“仅仅借助表明的观察就可以发现”,几乎不通过具体的数据就引出一个必然和肯定意味十足的结论,这就隐含了韦伯研究方法中一个较大的缺陷,虽然这与韦伯所处的时代的是分不开的。与韦伯同时期的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也在研究方法上受到学界的批判,“涂尔干的进路并非十分完美,与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研究自杀一样,这种完全忽视个体而完全从整体的角度考察问题,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对于自杀的定义,他只强调原因而忽视目的或意图。”同样的,韦伯在本书中也多从经验事实出发,强调从整体的视角考察问题。虽然也可以从另一角度为本书的论证过程不足作出辩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更像是一部逻辑自洽的理论文本——或者如韦伯自己所说,本书更像是一本“纯属导言性质的讨论”,因而“没有必要再堆叠更多的实例”,而非一篇基于扎实数据分析、进而做出解释的社会调查报告。
三
争议与思考
01
驳斥“观念决定论”说
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无疑是最为声名卓著,也最受争议的现代社会科学作品之一。”
的确有不少人对本书作出过批判。批判者多认为韦伯在书中对资本主义精神的阐释是一种“观念决定论”,认为韦伯将宗教和伦理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位置放置得有失偏颇。事实上,韦伯本人在其另一本著作《儒家与道教》中就对此作出了回复:“(下文将要讲述的内容)只是命题,而不是一种主张:宗教信仰的特征是一种单纯的因变量。通过因变量,这种特征可以把自身所属社会阶层的社会状况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来。”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分析得出韦伯写作的动机:他意识到宗教信仰只能作为影响社会发展因素之一种,而宗教信仰这一观察社会的视角是前人未采用、效果又奇佳的,所以他才对宗教信仰倍加以青睐。也正是因此,我们才可以看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家与道教》、《印度的宗教》与《古犹太教》等等以宗教视角研究社会的韦伯著作。
韦伯并不认为宗教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他将宗教看作一种动力,这种动力“深深根植于各种宗教的心理联系实际的行动之中”。同时,我们必须还看到,宗教作为一种经济伦理因素,其在影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要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并不能单方面决定经济发展。
02
表面经济形式与不同经济伦理的结合
国内一些学者在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时常常论及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以“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等文献材料和明清时发达的棉纺织业、矿冶制瓷业为例证,来证明在明代中后期和清代,我国东南地区的一些工业领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从而进一步得出“如果没有1840年的打断,中国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会慢慢成熟,照循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最终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虽然近些年来学界对这样简单的说法已有批判之声,但韦伯对此的认识,早已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提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的邓拓、吕振羽的前面。
在韦伯的另一本著作《儒家与道教》中,他曾提出:“表象上相同的经济形式与完全不同的经济伦理相结合后,所产生的历史作用不但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且具备各自独有的特征。”用韦伯的这个论点来解释明清时显露出的资本主义萌芽特征尤为适当。从表面上看,明清时存在的“(苏州)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等现象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情况十分相似,是表象上相同的经济形式。但事实上,前者与后者发生在情境拥有完全不一样的经济伦理环境。从政治方面来看,“重本抑末”在明清时期仍然被当作主流政策来加以推行,如“(洪武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纱”;从思想文化方面来看,读书人地位崇高,而商人则普遍受到民间和官方的双重鄙视与轻贱。反观经济表象相同的文艺复兴时期以降的欧洲,鼓励合法赚钱的天职论成为资本主义崛起时代的精神代表,发奋致富不仅不耽误对上帝的效忠与虔诚,反而成为作为上帝的选民履行天职之所在;克服了前资本主义状态的欧洲人也开始用理性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形式进行商业活动,紧锣密鼓进行的宗教改革也“使那些为了履行天职而进行的有组织的世俗劳动得到越来越多的道德重视和宗教认可”。从以上可以看出,明清时期与文艺复兴以降之欧洲虽然具有相同的经济表象,但二者拥有完全不同的经济伦理情境。所以,当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表象与各自独有的经济伦理特征相结合后,自然产生了韦伯所说的“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历史作用”。
四
结语
当代中国并非宗教社会,然而,日趋转变的现实也不得不令人重新思考宗教将给社会带来的意义:据2014年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在2300万至4000万之间。此刻,韦伯所研究的宗教伦理及其关注宗教的问题意识就更可为国内学者所借鉴。
五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2]方志远:《关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几点商榷》,中国明史学会第六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5年
[3]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4]刘燕舞:《自杀研究:困境表述、理论检视与进路转换》,《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5]王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研究方法探析》,博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伦理学系,2008年

附阅读书单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费孝通《江村经济》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
网址:网络社会学 |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https://c.klqsh.com/news/view/284777
相关内容
【理论探索】陈尧: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玩劳动”的生成逻辑与价值引导商业书单读懂 50 本全球商业经典管理类1.《追求卓越》(美国)托马斯·比特斯、罗伯特·沃特曼2.《 基业长青 》(美国...
电影鉴赏:阿拉伯的劳伦斯
哲学书目
生活与自由——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
哲学经济学推荐书单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审视生活
心理学书籍 [美]卡罗尔·德韦克《终身成长:重新定义成功的思维模式》完整版pdf/mobi/epub可下载
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当代价值
生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发展